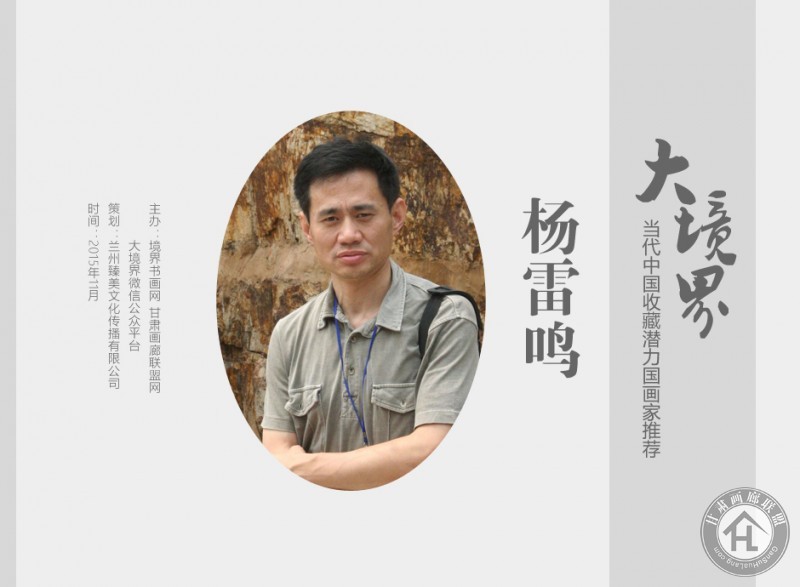编者按:画家杨雷鸣的绘画作品,以人物与山水见长,讲究画韵诗风书为骨,被誉为“新文人画——散文画儿”。他的人物画,多取材于军旅营地,结构严谨,形神兼备,是其大气大度,外和内刚天性的外化;他的山水画,着意宇宙精神的塑造,运用水墨的灵性,结构的张力,使作品大气流贯,意象横生,是其朝圣艺术,向往未来胸襟的喧泄。倾其于书画与为人,近日,甘肃画廊联盟网对其以微信沟通的方式进行了专访。让我们又一次深入地了解了一个来自军旅的年轻画家,一个有才华、有追求的青年艺术人才,他对绘画的执着与个性,对做学问的严谨与思维的深度,对人生的信仰与做人的乐达……不由心生敬佩。对他的回答我们不忍删除只言片语,因为每一句都带给我们很多的受益。为此,就本次专访我们以四篇访谈形式将其回答内容完整地呈现给大家,以飨读者。
甘肃画廊联盟网:您是一位善于学习、勇于探索的画家。您对古画心追手摹,悉心研究国外艺术名作,您又得杜滋龄等大家亲授,您觉得您在艺术创作上的成功与这些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关系呢?
杨雷鸣:首先对我绘画气质影响最大者,莫过父母对我早期的知识训练最有效最形象的手段就是学绘画。施胜辰老师“盖情足于墨酣”,杜滋龄老师“出新意于法度”,刘大为老师“承笔墨于恬畅”,任惠中老师“寄妙理于豪放”,五者之绝妙契合,方可使我的感情飞向一个遥远的空间……
古时的中国画,多兼诗与书,于是,中国画逐渐与诗、书交融,而形成一门画、诗、书三位一体的独特的综合艺术形式。
当代画家因受西式教育的影响,传统文化相对受到冷落,且素描教学多以“块面造型”。而与国画的“以线造型”大相径庭,因此,日常书写以硬笔取代了毛笔,而使用者也相对远离了毛笔书法艺术的普及教育。这样以来,就导致中国画中的画与诗、书逐渐拉开了距离,“以诗为魂,以书为骨”的传统艺术主张受到严重的挑战。
我们要把握画、诗、书的精神所在,并不一定要因袭画、诗、书三位一体的绘画表面模式,也未必要追求“树如曲铁,山如画沙”的艺术效果,但尚能细心品味诗歌艺术语言的高度凝练、概括、浪漫、夸张及其韵律的节律之美,乃至书法艺术中的“一波三折”,轻重疾徐的线质美,及其点划拂研,聚散呼应的形式规律,并将此融之于绘画,岂不“诗魂书骨”猶存矣?
我真正专攻中国画,还是在我步入军旅之后。开始,我师承中国画大家杜滋龄。继而求学“军艺”,受到中国画大家刘大为、任惠中的悉心点拨。于是,我以绳系日,朝研夕磨,一晃就是半生。如今,我信手涂抹,虽不能苍劲腴润,腕底生辉,但也笔不着纸,力似千钧。因此,我所创作的每一幅画儿,从无“一挥而就”之说,而都是“精心策画”的结晶,又都是力求画蕴的意象化、散文化,表现“天人合一”的永恒主题。
杜滋龄先生对我十分器重,对我的白描作品也很欣赏。杜先生以他深邃的艺术思维和精湛的艺术技巧,以他豪放的为人气质和博大的水墨造诣,深深地感动着我。我那时十分幼雅,求知欲望十分旺盛,对于杜先生这样的大师我是高山仰止,把他视为神灵。一次杜先生看了我的白描稿,便送我一幅大作《八十一难》,用唐玄奘西天去经,不畏八十一难的精神激励我知难而进,义无反顾。我授之动容,更感到杜先生灵魂的美好。对我一生有知遇之恩的,他便是其中之一。
记的那是我第一次和杜滋龄老师去西部高原采风,茫茫大漠,雪域高原,黄土高坡的神奇、斑斓与醇厚,使我犹如大海行舟,眼底涌动的瑰丽浪花与海天一样壮美,似乎一下看到了遥远的彼岸。
我从早到晚沉静的坐在沙丘、冰雪、草丛上,或凝视着远处摇拽的红柳,或凝视着草地上云朵般的羊群,或凝视着正在转场的牧民驮队……
在这沉静的背后,我心底的燧石不时地敲击出灵感的火花,我生活的河流又不时地翻涌出艺术的浪花。
辛勤耕耘后有所收获的时刻,我从浑厚的黄土中发现了土黄色的高贵,从赤热的砂砾中发现了赭石色的凝重,从如茵的草地上发现了绿色的柔美,从碧净的天空中发现了蓝色的壮丽,从如火的霜叶上发现了红色的热烈,从皑皑的雪原上发现了白色的纯洁,从藏胞黝黑的皮肤上发现了黑色的拙朴……
靠我当时的能力是无法抓住托举这些色彩的线条,并用这些线条编织生活,编织着绚丽的绘画之梦……
梦,总是要圆的!在杜滋龄老师指导下。我如饥似渴地倾听、思索、创作。紧张的学习生活,使我理解了传统,认识了自我。
在军艺,我接触到刘大为、任惠中老师。刘大为是我军艺美术系的主任。他性情宽厚、热烈,心中像是蓄满了温暖了的阳光。在学生面前,他得宽厚近乎骆驼,他的热烈如同骏马,素有“骆驼刘,大为马”之称。是我学习的榜样。
在军艺,对于我这个一直编织“西部梦”的军旅学子来说,当然对西部生、西部长,被称之为“西部通”的任惠中老师十分投缘。
长期以来,任惠中老师的目光也始终投向西部风情,笔下始终未离开雪山、藏胞、牧场……。显然,他是在追慕着一种苍凉与犷悍的画风,其作品也隐潜着生命的艰辛与悲壮这一重要题旨。
具体说来,应该是那种对西部高原景观与习俗风情的体验,已成为他刻骨铭心的震憾,已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与精神资源,并促使他在艺术选择上,走向了苍凉与犷悍;在艺术语言上,产生了由写实到写意的转变;在审美的取向上,他毅然追慕着整体、浑然与大气的美感。
这就是“任惠中艺术”,不好说的神韵与说不好的自信。这就是我面对任惠中老师教学与作品的痴迷所在。因为他没有停留在我的视野上,他像一个机灵的猎手,始终寻找着涉猎的最佳位置,留在地上的始终是一串求索的脚印。顺着那串求索的脚印,我睁大双眼,凝视着任老师的教学与创作:
其一、我看到了任老师作品的文化底蕴——藏胞的游牧与朝圣,永远是一种出发和向往,这样表象的典雅、轻灵与流畅在笔端消失了,“语言”诗意转为内在的韵味,作品获得了拙朴、苍凉和犷悍的艺术特征。
如此而已,不过、为的是更好地表达客体生命处境的严酷与艰窘,生命力的顽强与坚韧,这无疑是对民族文化底蕴的把握,是无法取代的“大美”。
其二、我看到了任老师画笔的多变,卧锋横斫与皴法质感的浑融运用。
他以“无序的有序”为法则,常在纸面上做胸有成竹的秃笔点染皴擦,以将错就错的不定性来铺排画面,且因势利导,因形用笔,结构紧收,以实现作品整体的浑然感。
其三、看到了任老师有着较好的造型基础,且速写功底极好。因而,他善于从速写的线条中提炼笔法。
特别是短线的运用,以结构与感受为框架,在重复、堆积、选加中造成运动感;线的飞白效果与波折的节律变化,产生的不确定性十分具有笔墨个性,有力、有度、有神韵,有节奏的传达出感觉和情绪;
同时,线的组织与墨色的分布,更见其苦心所在。
其四、也看到了紧紧抓住“远观其势,近观其质”这一画理,是任老师作品的又一特色。从这一理论上出发,他苦心孤诣地把山水画的皴法与用法应用到了人物画上。
只要仔细审视任老师的水墨画,不难发现,人物面部的沧桑感与风霜粗砺的犷悍气质的表现,确有山水画皴法的借用,并表现出一种冷峻、坚硬的硬汉风度。而藏胞皮袍的肌理与质感,同样是由山水画技法转换而来的。他笔下的藏胞因为山水皴法与笔法,而产生出一种岩石般的冰冷与坚挺的感觉,从而塑造了一种皴具阳刚之气的生命形象。
军艺生活结束了,“西部梦”也圆了。我似乎通过刘大为、任惠中等诸师不断转换的朦胧的绘画语言,也从西部高原,寻到了一种源头、真实与永恒。
更重要的是、在这个观念自我、技术自我与社会文化、时代精神之间,做着自我抉择的时代里,绘画艺术对西部题旨的发掘,无疑是自我生命体验在时代背景和精神环境中的转换。这一转换和几位老师密不可分的。
我这一代画家,既是传统文化的孑遗,也是现代文化的创造者。任重道远、使命沉重,在艺术创造过程中,万万不可放弃的,是对自我的追向与否定,应该时时询问自己,“我是哪个时代的画家?”
杨雷鸣,1963年生,河北宗邑人,武警天津市总队师职大校警官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,天津美术家协会理事,中国武警书画研究院研究员,天津市政协书画研究院常务理事,天津市作家协会会员,天津市“十佳”青年美书家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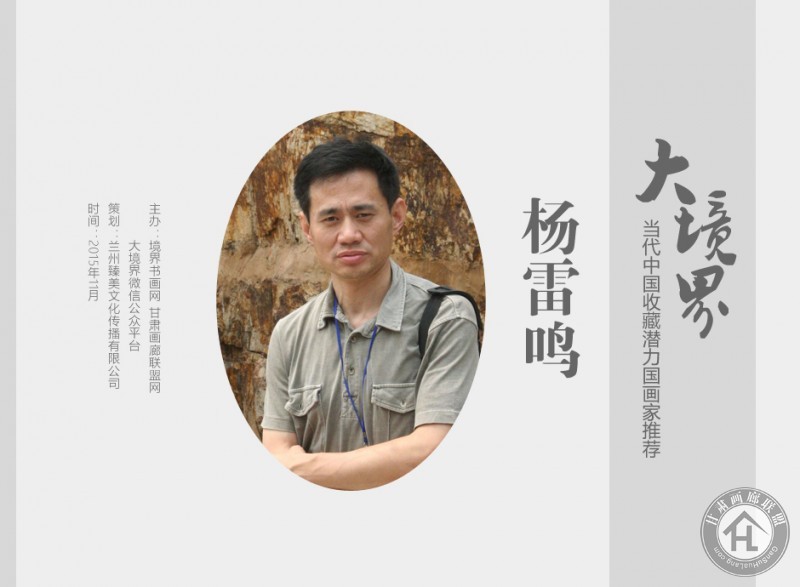
点击图片进入作品展厅